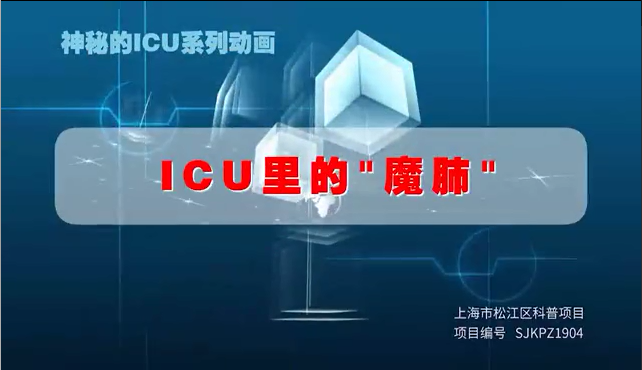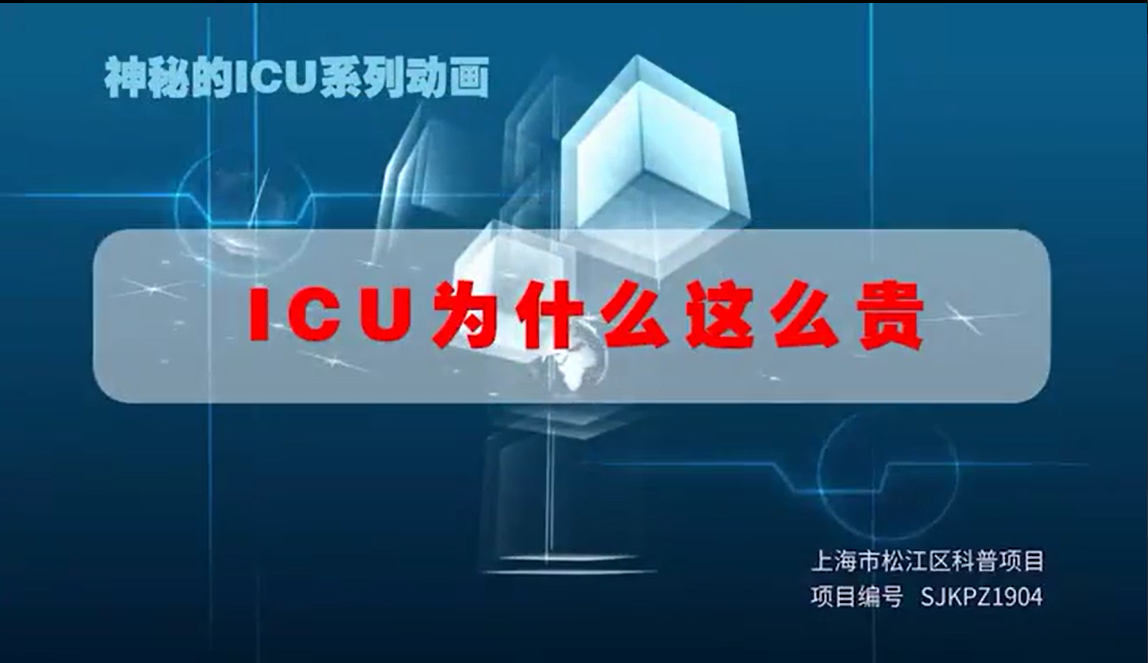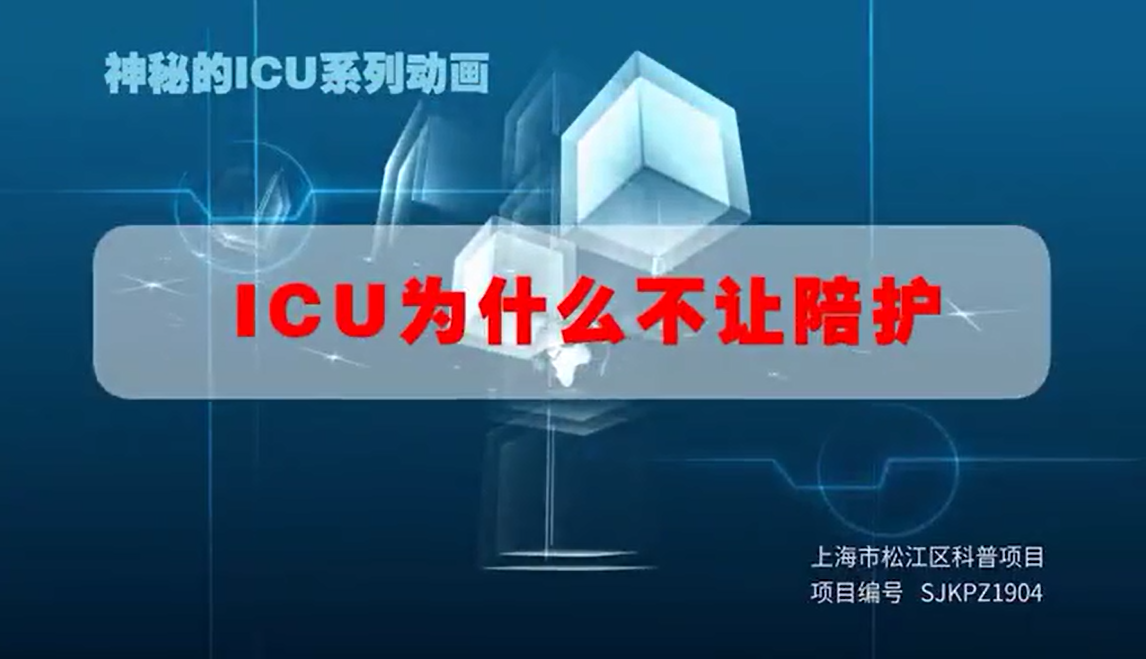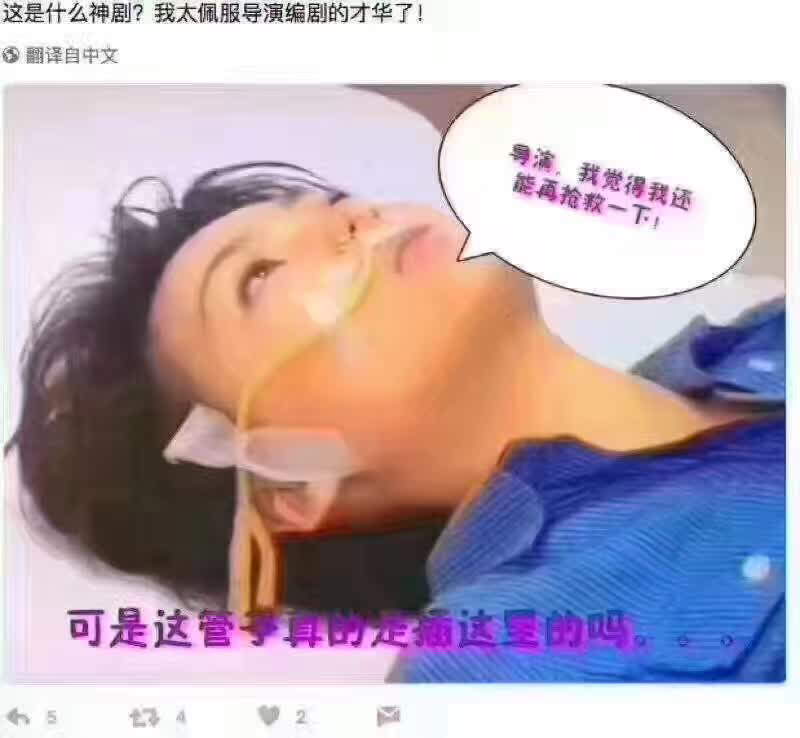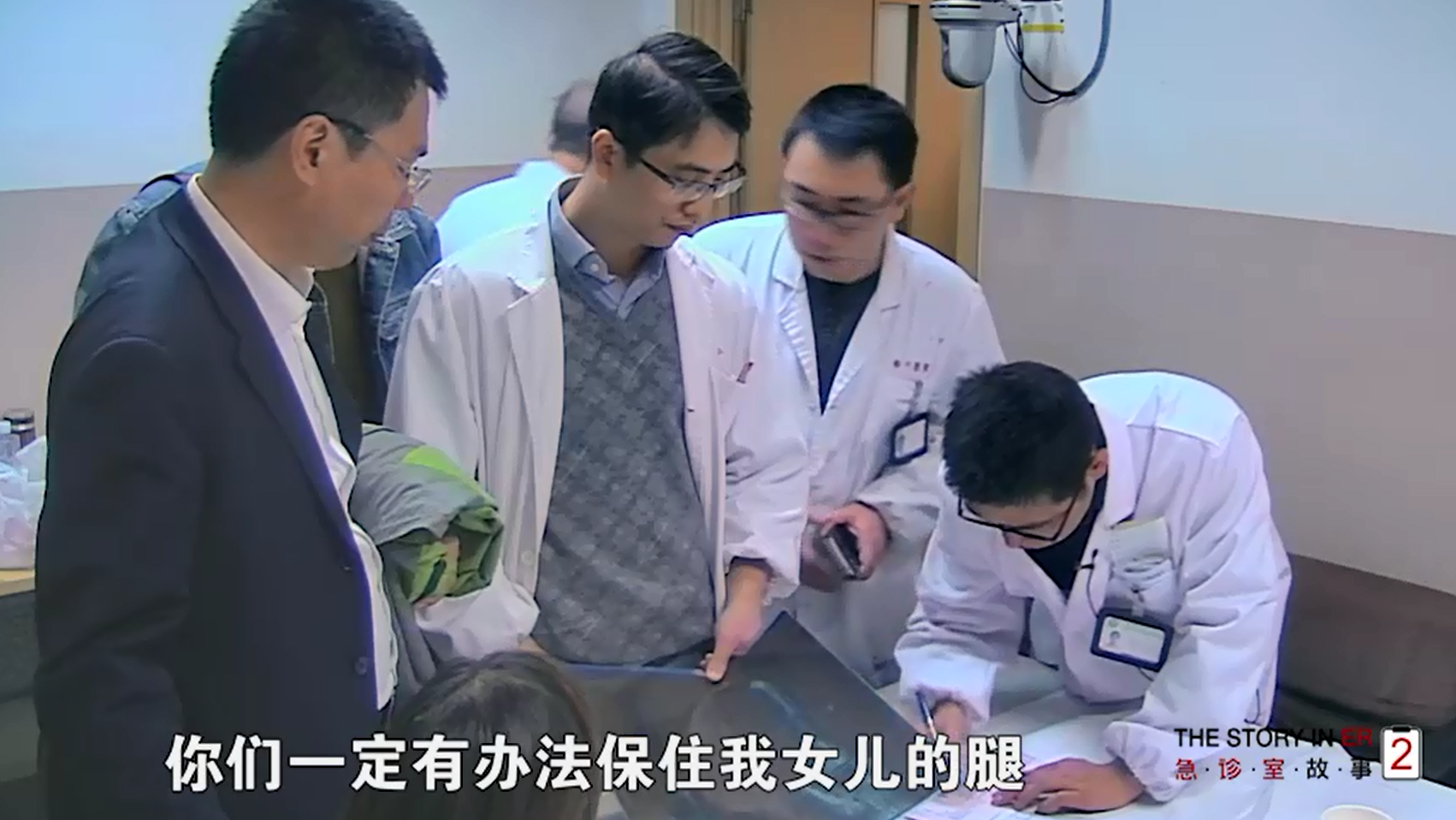5.手表
黄小桉的肩膀本能地变得非常僵直。但是,还没有等到她反应过来,卡门医生已经走远,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载着她绝尘而去。
黄小桉张了张嘴,刚才的情形实在过于古怪了。卡门叮嘱她不要遗失了那个小水晶球,那么,今天下午在地铁里遇到的那个奇怪女人,就是刚才共进晚餐的风度翩翩的巴塞罗那圣保罗十字医院的卡门教授了!这个跨越度未免也太大了一点了吧!而且,这位医生,怎么下午没事干游荡在地铁站呢?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小水晶球到底是怎么回事?黄小桉下意识地摸了模裤子口袋,嗯,硬硬的小突起提示着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是真正发生在她身上的奇遇。那么,卡门是怎么知道她从米拉之家顺手摸了个小水晶球?难不成下午她也在米拉之家?不会,肯定不会,她明明前后张望看清楚了没有游客注意,才把那个小球塞入裤子口袋的。而且,下午米拉之家的游客也并不多,也没有一位游客是打扮成吉普赛女人的模样的。
她欲言又止,不晓得是否要跟何赛讨论。思考再三,她这样开口问了何赛:“卡门医生很美啊,哎,你说她对中国的经络非常感兴趣?”
何赛说:“是啊。卡门医生是我们科的资深专家,迄今还是独身,除了研究看病、做学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潜水。每年都到很远的海域去潜水。别看她看上去挺温文尔雅的,其实她不太喜欢跟人家交往,只是这次,我提及你从上海来,她非常感兴趣。奥,对了,卡门医生是对中国的经络啊中医啊挺有研究的,以前她还专门去过上海学习过几个月呢!”
“奥……”
满腹狐疑中,何赛把黄小桉送回了宾馆。
已经十点半了。黄小桉回到房间,感觉非常疲劳,但精神却异常亢奋。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实在太离奇了!她一屁股坐在床上,又顺势躺了下去,倏然感觉到裤子口袋里的那个小球实在硌得慌。她掏出那个小水晶球,放在台灯下仔细把玩。黄小桉对珠宝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但是这个小水晶球在灯光下晶莹剔透,不含一丝杂质,纯净透明到了极点,仿佛是一小团凝固的空气,又仿佛是放大的露珠,这样的水晶球,应该是很值钱的吧,那怎么会让她随随便便在人流熙熙攘攘的展厅捡到呢?
她左思右想,实在不得其解。
洗好澡后,居然倦意全无。她吹干了头发,撩开窗帘一角看夜景。晚上的街道冷冷清清,拐角处是青年男女在幽会吗?女孩子靠着围墙站立,男孩子面对着她,用手支撑着围墙,低头俯身下去,温柔地吻着女孩。
黄小桉的心,忽然疼痛起来。
不能想。不是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吗。她在心里告诫自己。下面街道的情侣,男孩子的背影,乍一看,跟周建辉有些许相似。黄小桉第一次去上海中医药大学方舟教授的实验室时,看到一个男生坐在方舟教授对面的电脑旁,他的背影就是如此。周建辉的相貌让黄小桉过目难忘。他的头发柔软而且自然卷,很长的睫毛,很亮的目光,洁净的皮肤,配上修长的身材,随意的服饰,以及带点玩世不恭的戏谑表情,实在难以让人想到,他是著名的方舟教授的得意弟子。所以,当方舟教授对黄小桉介绍,他们的合作课题将具体由这位周建辉博士跟她合作进行的时候,黄小桉的心中情不自禁冒出了诸多问号以及感叹号。
当周建辉到黄小桉医院的动物房去看她已经饲养的大白鼠时,黄小桉对身边跟着这样一个家伙十分不自在。参观完后,又商议了后面合作的细节,时间就快中午了。黄小桉礼节性地问了一声:“哎呦,都快十二点了,要不,在我们食堂简单吃一点?”她想,两个人一点都不熟悉,周建辉肯定会婉拒。
谁知道这个家伙立马回应:“好啊好啊,早就听说你们医院餐厅的小炒很不错!”
到了餐厅,周建辉居然自己翻着菜谱点起菜来,黄小桉沉着脸,心里气呼呼的,眼角瞥见左右前后各种同学同事走来走去,看着黄小桉跟这么个男士坐在一起,目光中充满了各种猜测和笑意,搞得黄小桉简直坐立不安。好不容易吃完了艰难的午餐,结账之后,黄小桉赶紧跟周建辉说:“我下午门诊,就不送你了,咱们再联络!”
那个中午,在黄小桉的印象里如此深刻,每个细节迄今回想起来都纤毫毕现。是春日的正午,餐厅外面郁郁葱葱,有混杂的植物香气氤氲袭来。周建辉站在屋檐阴影旁的阳光下,他自然卷的黑发上闪烁着细微的亮光,他长长睫毛下的眼睛也在发着光,他看着黄小桉不说话。静止停顿当中,黄小桉的心灵越来越慌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啦,难道是她吃饭把脸吃脏了吗?就在她惴惴不安中,周建辉眼底的笑意越来越浓郁。要死啊,这个人随便说什么都没有个正经样子。他居然,他,一个著名的方舟教授器重的博士研究生,对她开口说:“小妞,你就这么希望我快点走吗?”
春风吹过。餐厅前面的苗圃中丁香也开放得过于恣意了吧,黄小桉简直被那馥郁的香气熏得有些窒息了。在慌张、缺氧、不知所措中,她居然被这个第二次见面的大男生就这么牵了手。周建辉拉着她说:“我们学校食堂的晚饭很难吃的,我晚上还来你们医院吃饭吧,你不会拒绝的,对吗?这样,我买单好了!”
黄小桉回想他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底仍然有着藏匿不去的戏谑笑意。所以,在后来的两年中,她无数次对着周建辉追究她的各种疑惑。周建辉每次都是这么依次回答她的问题的:“缘分。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都是有缘分的。缘分来了,第一眼就看清楚了,水到渠成。”“没有。真的没有啊,你知道我们方老板是工作狂,我从硕士入学第一天起,就没日没夜跟着她干,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去沾花惹草啊,如果不是她跟你们老板合作,老天爷安排你过来,我恐怕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小妞?喊你小妞怎么轻浮了?难道喊你小姐不成?哈哈哈哈哈!”
点点滴滴,在这异国的深夜一齐涌上心头。黄小桉内心惆怅感慨,两年多时间,七百多天,她与周建辉原来有这么多难以割舍的细节。和煦的灯光下,她抚摸着腕上的手表,愈发感受到人在异乡的冷清。
这是一块劳力士机械女表。经典水泡眼款式,不锈钢表面和表带简洁大方,是周建辉帮她买的。刚刚博士毕业的大学助教薪水清寒,这块表几乎花尽了周建辉的全部积蓄。他给黄小桉戴上时,黄小桉嗔怪不已,“这么贵!干嘛要买这么贵的呀,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呀!”
周建辉嘿嘿一笑,“既然买,就要买最好的么。钱是身外之物,让你好好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光!”
黄小桉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不是正因为周建辉身上这种一般理工科男生身上罕见的放荡不羁的气质牢牢吸引了她。周建辉无疑是非常聪明的,这从方舟教授对他的格外器重上就能看出睨端。不过,他跟周围其他人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他散漫的性格。他那种无所谓的样子就像一块透明的水晶,从各个角度都能折射出女生的爱慕。黄小桉去中医药大学的次数多了,深深的体会到,其实,投向周建辉的女性目光还是很多的。所以,她总是会追问周建辉既往的情事,每次都一无所获。后来,她安慰自己,既然现在两个人很快乐,那就可以了,女人只要男人的未来,只有男人才关注女人的过去呢。
可是,就在她戴上这块昂贵的劳力士之后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事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年年初,两个人还兴高采烈地商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就在五一先把结婚证给领了,至于结婚仪式么,等到合适的时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开春再说。可是,就在春节放假周建辉从老家回到上海之后,一切天翻地覆。
如同当初周建辉毫无征兆地牵拉她的手喊她小妞那样,他忽然变得跟她非常疏离。电话开始打不通了。短信不回了。微信上基本没有消息了。黄小桉实在无法接受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状况持续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方舟教授打通她电话,说要跟她聊一聊。
黄小桉赶到了方教授的办公室。方教授年届花甲,短发梳理地整整齐齐,她坐在电脑椅上,拉着黄小桉的手,说:“小桉,这…….真是造化弄人。我也喊了周建辉过来。你……要理解他的心情。小桉……看样子你们俩必须分手了。周建辉他……他们家有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家族史,你知道吗?”
宛如晴天霹雳,黄小桉感觉自己的手在方教授的掌心逐渐丧失温度。多发性神经纤维瘤,是的,周建辉跟她提及过,他父亲就因为这种疾病而过世。当时,他也表示了很大的困惑,因为这种疾病是遗传的,不过,迄今为止,周建辉身体都非常健康,遗传性疾病嘛,也有可能后代会遗失这种致病基因。难道,难道,难道周建辉现在他出现了什么异常?
看着黄小桉绝望的眼神,方教授惋惜痛心地说:“是。他……出现了初步症状。他父亲早逝也是因为这个毛病。所以,同样学医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让他坚定了学医、而且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方向。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良好,但是,就在上个月回家时,他母亲发现了他跟他父亲年轻时如出一辙的表现…….”
黄小桉扭头,泪眼婆娑中看到周建辉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倚在办公室的门框上。他的神情非常平淡,仿佛方教授刚才叙述的跟他没有任何关联。等方教授也看到了他,周建辉一如既往很不在乎地走来坐在方教授对面的办公桌上,看着黄小桉说,“小桉,方老师都告诉你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重新回到原点吧。你怎么可以跟一个多发性神经瘤病人在一起呢。而且,我们的合作课题也已经告一段落,后面的步骤,是我的范畴。”他的睫毛依然很长,目光依然清亮,他深深地注视着黄小桉,黄小桉觉得他的双眼仿佛两口深邃的井水,她筋疲力尽也看不到底。周建辉对她说:“小桉,我们共同走过了美好快乐的日子,但是,现在,这段欢乐的时光已经结束了。我们是成年人,必须要接受事实。我们都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对方。你不可以跟一个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病人结婚,我,也不会让你跟一个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病人结婚的。”
说完了这些话,他扭过头去,再也没有看过黄小桉一眼。他对方舟教授说:“方老师,自从考取您的硕士开始,硕博连读五年,工作一年,我跟您在一起不知不觉都六年时间了,我象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尊敬和爱戴您。今天您也在场,我都把话说明白了,小桉是个好姑娘,我怎么可以拖累她?我们今天开始,不再会有任何联系和交集。不过,您放心,您安排的合作课题,我还会继续努力地进行下去。”说完这些,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
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黄小桉心里如何舍得?她的心里百转千回,心想生病也没有关系,谁还不生病?可是,转念之间,就算她不在乎,可是父母呢?父母会让她终生陪伴一个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病人吗?还有,孩子。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如果孩子也不能幸免,那可怎么办?她会想起收治过的神经纤维瘤病人,那种景象还是让她心有余悸。且不论病人体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脑膜瘤、胶质瘤等,他们的皮肤会发生各种色素沉着,典型者呈牛奶咖啡斑。更为甚者,病人的身体各处会出现无穷多的小则粟米状、大则葡萄状的突起,浑身长满这种红色、淡红或紫红色、质地比较硬或韧的结节,连脸部都不能幸免。曾经有一次,黄小桉收治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男性病人,他终生未婚。黄小桉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无能为力的巨大悲哀。她让病人解开衣服做体格检查,病人抵死不肯,一边嘴里还念叨:“医生,我很丑,我太丑了,我是个怪物……医生啊,我家里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只有我是该死的怪物……”一个门诊看得黄小桉擦完了所有的纸巾。
沉默。不知沉默了多久,方教授用她温暖的手掌抱住了她颤抖的肩膀,“小桉,建辉是对的,你要学会面对现实。”
这样静谧的异国的夜晚,黄小桉无声地泪流满面。她听他的话,听方教授的话,面对现实了,可是,她的心有多痛,他们知道吗?
腕上的机械表,滴答滴答地走着,提醒她无论怎样时间都会客观地流逝。她走到卫生间,洗了个脸,给前台打了电话,预约了明天早上七点钟的morning call。奥,确切地说,是今天早上的morning call,因为手表告诉她,现在已经是临晨两点钟了。
黄小桉睡得一点都不安稳,估计全部都是浅睡眠。morning call响起的时候,黄小桉疲倦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来。她顺手挂掉了电话,告诉自己再睡十分钟。
过了一小会儿,黄小桉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今天开会可不能迟到。她的导师陆鸣教授和方舟教授,应该是昨夜到达的巴塞罗那。不巧前三天正好是上海市医学会的神经内科年会,这两位专家都脱不开身,只能等年会结束了,才能过来参加这里的欧洲神经内科大会。今天上午,陆教授和方教授都还要在各自的论坛上做学术报告。黄小桉原本自告奋勇要去机场接他们的,但这两位不约而同地说已经相互作伴,而且,以前都曾经来过这里,让黄小桉有空还是多抽时间顺便玩玩看看风景。
她一边穿衣服,一边随便瞄了一下床头柜上的手表。咦,是看错了吗?她连忙拿起手表看个究竟,怎么才四点四十三分?可是,刚才,明明已经morning call了呀?她不可置信地又查看了一下手机,手机屏幕显示,已经是上午七点一刻了。
作者:程蕾蕾





 收藏
收藏
 赞
赞